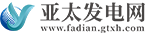
再过十年,琛还会来。
二十年,以后,琛也来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琛现在站在块泥巴地,到处水,一汪,不像从前,干的经常想世界末日。
他们都在个敞院生活。
琛外,分别是1,2,3,4,5,6,7,8。
琛不记名,记不住,就排号,搞不混!琛那年就说,她搞不混,经常的,琛念完这句,心扑扑地,脚底就在一处儿丫板凉凉,心上痛快。
琛早留起头发,想到这,得亏长头发,接着就遮盖,那时她又差点想哭,琛马上撩眼,一只雁从琛眼球里通过,留下块极其规整的小云彩,云边齐,就是个荷包子,这时天发水釉,绿云一朵,两边白,一朵在琛眼中,一朵现在底下有树陪衬,是纻树。看够了,琛就走。
1开始说话了,琛马上感动,抓了抓这时乱发,风不听,连续吹,动过来,跑到琛手背上,她往后看,净树,净湿土,一条惨道,还是她决定要走的,坑坑洼洼,泥水。
就喜欢这。一辈子我能待在这儿。1终于说完,琛笑,头发反正不听话,就不扣它,风又过来,太阳居然也有了,这时琛真掉了泪,迅速掉下来,下边是湿土,落进去。
林斯莫尔郊外,贝克斯希尔采石场,废弃的采石场,砂岩峭壁下,蓝色水域。
琛往哪看都开始是,绿线,都是树。
中间有道折,像照片突然折掉,断开画面,两边是树,琛在看回忆,树嘛,还是峥嵘,叫不上名,仍坚强,正迎接远方回来的人,以前这净2,3,4们,都是女孩,地下也干。
地上,开始有车辙印。
琛叫自己闭眼,她闭上眼走,就开始高坡,被坑坑下,就笑,马上有右脚,一小抻,提出左脚,没有吃泥声,脚心慢摸出道道,大部从坑下深的地走,越走越好,不被坑实,琛这就来到坡顶,她忽然害怕,猛睁眼,后边确实没人,她想起,5,6,7,8都整天泡在水里,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。
重来瞻仰,也就琛一人。
琛开始努力想这些人,1应该是叫露,2就是水,3是因,4是园,5叫依,6是贤,7叫乾,8是阿,他们不知道,这是琛的外号,她们也不知道,包括琛,都是外国人,这样好记。
那年,琛不知道也是种姻缘。
露长的像小孩,是个孩子,女的,胸部没发育,肚子有了,要命的是,她经常在穿比基尼,粉色,上边兜不住,下边圆出来,上下不对称,接近胸衣底的右臂,生块迹,像嘴,刚喝上艳口红,印上去,抽忒快,上边一条线,下边是肉,整天驼半臂,表情慵懒。
水浑身雀斑,脖子有才起的痘,特别新鲜,周围撒满雀斑,有些恶心,实在像泥,每天甩不净,挣扎一身脏水,滩上,和出些边,深的深,浅的浅,像无处插脚的沙滩,他脖子窝也有痣,有次琛看进去,以为是露那种,过会不如露温柔。
因有一次怒视琛,琛现在记起,那时她就在绿水中,的的确确什么也没干,因偶然回神,就以为她看上他。他留长发。
园最可爱,是个小小女孩,直到分别,她都挂绷带,没换过胳膊,左肢,琛最记一层黄,她上褂,下一圈黑,小布裙子,围不住腿儿,再热不穿比基尼,穿两样袜子,粉的脖高,白袜舀小,都卷在桶鞋,黑色皮质,就像邮筒,琛觉特别沉。
依是男孩,没什么特点,老拿起个水汽球,挡他腹部,他肚子不算太鼓,他嘴噘。但是好人。
贤穿淡紫比基尼,胸部发达,脸也发达,一个水舀子,从鼻下开始豁出瓢水,嘴都送过去,头顶往后无限扬棕发。
乾经常失意,因为她有时感觉阿喜欢乾,但在水中,乾就经常被见这时阿从不看乾,嘴下怀里都是另外一个人。
贝克斯希尔采石场不小,人不止这9位,以后大家都会知道。
有位亚洲女士,她像假发,好摄影,一个人待绿湖能论天,不过鞋不换,成双妖粉球鞋。琛总感觉她神秘。
琛往右看看,头发接起她眉毛,她再往左看,对边没过来一辆车,琛的裙边撩起点,她穿的红白扛,一阵车卷走些灰,马上扑到琛红裙。
今天梳的发到耳朵,几辆车过去,她看见好几回,自己模样文雅,和那年没变,现在她注视地面,就不远,每次车走完,大轮胎右边,欠水泥,凹进去,冒根豆芽,底下青草棵子,到花萼,套豆芽,真是采石场附近特产。
琛打量窗外,这时都有下午太阳。
上车后没几人,这还上午,大家就都不在,琛努力看窗外。
还有个人,印象极其深刻,她不大说话,但眼会说,一整年中,她都老实,长得也好,梳波波式,好穿绿衣,绿眼,长相总在等,没有得到,总在温柔。
琛好在绿湖边踫她。
车走不几站,就是片湾,这种地方这么近,琛一年里没见过,这时琛小惊,她们宁愿守着个枯湖,这不远就是海,这里静,太静,除了海小湾子,根本没什么,天上不见鸥子,远近没桥没亭,乱乱几棵椰子树。
她们是热带。
像热带。有时会有许多花,突然出现,窝起,存个洞,黑里是花乱,外围糙,一片紫花,跃跃威威,不高,地肤子,开小淡紫花,窝那边,成片出种黄桔藤子,有时这里会忽然冒出露。
静悄悄的,像片瓦。
看住棵就发神,琛也喜欢,她想问她家人都有谁,但很怪,经常几次看花,被花截走,那时不是琛旁风晃,就是露她再也不想,回到一片林子,下边小桔豆,上边像个荷花,她长得美,特别白,一朵花,有很多时候露十分成功,错过去了。
这时车上人,她很难,把提包掖进小过道,总算刚坐身,晃晃闪闪,颤的头乱摇,对视琛,琛想这就是30年后露。她戴眼镜,露不戴,她还小,以后戴,坐辆高贵、刷黑漆车,当富太,架上金丝眼镜,头发拉直,不再乱篷篷,琛有时给露对话,说过,她这回也说过,琛记得,她永远是这里人。
林斯莫尔郊外,采石场有蓝色水,露这辈子她忘不了,这种地方又增加了,这时琛还想问露,她想过等等,过早晚她会见上露的真正父母。
露经常跟着的,不是她家的。
有一个女的,长相偏软,随时要塌落,琛替她出场端着,每回有露大部时间都是她,琛这气得端到她消失,那时女士经常发呆,再就是看天,露没介绍,琛看出她就是某电影上,喜欢写诗的人。
紫色裙子,绕满花枝,有双粉鞋,手很好看,经常守湖,湖那边是梯石,有时琛会害怕,她不怕,一站小半天,她都在端相机,猛朝一个方向,那时她脚底净草。
琛想扎得慌,太阳正发威,无时无刻,粉鞋上挂满江,挂满太阳,露出现时她偶尔看旁边,再端起相机。
你爱作诗么。
你不上学?
这种问题大都消失,大家目标一致,跑到世外桃源,匠心独具,琛托起了腮,得架前边空管上,还是后年夏天,管子都不凉。有时她就摸露。
她皮肤,她开始揉搓。
露也不生气,没太高兴,那时她好看天,她就不看天,她摸着露想事,眼神难得涣散,露呈现成人舒适,看见远方那都是海,也不闭上眼,脸相懒上来,被搓烦了,就短暂推开,不多久一只手回来,露看着发痴,眼前一片小草,没花,几串鸟叫从天上窜过去,特别清脆。
这次回来,琛没有目标,她想,就是花费一天,重复在坐公交,再20年,39年再回来,她也坐这种公车。现在琛找到新工作,不知道那些人。
附近有采石场。啊!?还有采石场?不是炸了。炸了!那不可能,那可是个奇处,现在也没有那堆闲人了。说完这话,胖男人满意,使劲的,结结实实靠上了座位。
闲人你说闲人?你谁,不是闲人呢,假露又意外回头,琛没想她给了个台下,假露结结实实回过了头,她那边还是高椰子。
这周围怎么净海?我是说以前。
你说话别太聪明,好好好,我知道,满车里都是笑。琛窗外是绿湖。
很多时候她都找不到露,她经常突然出现,琛也吓不着,后来等见那片更大湖,露说这话时少,经常特别喜欢眼前,琛第一次见简直给震住。
哪有这么大湖!
一片波蓝,说绿不是,大部分有朝向,推层细水,波上来,涌涌,这时水面就掺风,也细,又推,看吧,那波小面是块纱子,也就是纱,舀前舀前,根本不露,全拥在表皮,下边又是绿,印度宝石绿,没有下边,上边无穷波。
琛找这湖前,没有那个摄影师,露也不全说,这人来历、这个留变式波头女人,越发神秘,但不讨厌,琛说实话,看不见她或看着别人,在水中闹,老想这个人。
想到她就想那种石头,她说就像恐龙,她也这么说过?琛有回好歹有机会问,露第一次正面稍稍介绍,她不是我母亲。
下边琛就不好问。
她总爱找石头。
往后露会经常给琛说,家摆的,里三层上六层,到处搜罗奇石,石头得实,这就特别占地,她也不在乎,或说非常在乎,跟露这些年,老带起露往那有石头地跑,琛听出露家世不简单,她说她不是她家人,但常跟露,这都使琛想到中国有本奇书,里边也有个人找石头,叫石清虚。
琛问露她都怎么个爱法,琛比较一下发现,表面上神秘而已,她是为这一片景致而来,而她们来了就专注起来,琛到现在发现不了某一种物事,就是说她爱这里的一切。
我也爱这一切,就——她撩动小胖指头,随便一指,都是些绿,树啊草啊,有时飞的东西琛看着像绿,展现在面前的,我都爱。
琛看了看这些。
她有点后悔,和露说话有段时间,绕在她俩跟前的,都不认识,都穿一种衣服,比基尼,还好都是女人,但女人也有凶比男的,她们窝腿,踹起些小眯浪,也不知道露试出没有,呯她身上不少,天也热,谁不在乎架势,她们肆无忌惮,继续动水,露继续给琛讲这个女人,她们也听到,另外就是些树,可大,包起她们,毫不费劲,也不留情,看的着荫凉,在远地,她们下水旁,都是大干石头,大干太阳,慌慌下,晒后背,哐哐地,石头也耀眼,后头树倒绿,有时琛不看后,不看左,右也树,她闻得到深森林味,但触不到跟前。
有时她想我们怎么不到树底下呢?
这里开阔,一会儿琛就想过来,那有树的,下边也湖,但生草,且成势力,汪洋洋一片,不绝,下脚地没有,琛但有时好像有点留恋,经常泡水脚,眼朝有树地看,琛看着那边向这边露答。
没有目的地,琛下车了,也可能是次偶然,她真下车了,幸亏还有个摊,这么热天,琛就买上个球,立方体,香草味,她也很满足,眼下她感觉刚吃过一个,那片绿湖也算。
琛坐在条单独凳子,一舌头进了,有冰鲜草莓,一舌头有松香,她想这次休假有限,她也再找不到矿石花园,就光在个脑子逛了。名不符实,琛随着一辆车玻璃走掉,收回这个念头,这不算,算热的,琛咽进口浓雪糕,从食道过了胃,她有点悲凉。
琛想走走。
她就走。
这里也不繁华,小村小镇上,能有的没有的都也在,出点摊算好的,琛就走走,过站几里,居然还有游乐场,也废弃,电动马,光彩明人,童话也会凋,干不干稠不稠,挤到这里,上边灯泡没有土,下边都是亮马子,琛阻止自己去想小孩时。
她给那个有绿眼的说过马。
她更……琛不好定义,踫上有露有琛,她先笑,就笑笑就过,踫琛一人,她也没在找露,她就真过来,坐下来。不用问她说,她失业有年,才发现这么个好地,琛才问平常伙食,她又笑,真轻,琛这时会迷住,她眼太美了。
你也好看书。
她扬头发,眼都平起,又温柔,周边都是水。
看书也没什么用,琛差点没听到“什么”,转身这时,就是她那个手,正离琛手不远,压住张掉叶,里边净汁水,她手上走红,她是白人。琛想她是说了什么,没什么用。接着琛肚子打量,她不过20,要不就才16,先辍学了?也不好问。
打算住多长,这个琛没问她先答,她坐的姿势舒服,给人个美体子,这也是资本,她说先看看,她是在网上听说有这里。
往后俩人都在看这种绿。
你看后边,这后边,是田野啊,她又先说话,露在那边,更不远,她又再说一遍,过去你家种地么?这其实用处也不是太大,琛也想先答,又压过去,露想过来了,她半笑撑地,不容易,最终起身,笑迎着露又走开我们。
那是夜,她住棕帐篷,挨琛近,晚上,绿湖更蓝,水深有东西,看!蓝呢?她经常说着就过到琛边,琛也睡不早,俩边闲,就拉拉童年,光辉日子,太平,说着就有匹马。
她有时想让马出现在她绿眼,就真给看到,琛眼里也有两匹,都关在高铁笼子,外边会是小树?不过年份远,她年龄也算,看小树是森林,感觉万马千匹,都是两棵树,现在当也不高,那时高,就俩棵,应该是梧桐,匹马争豪啊,枣红在前,白马吃灰,变黄,永远搁后,电动一响就会跑,不知疲倦,琛总看那匹红马,特别高尚,老是扬头,不扭头,不照顾,白马,那个白马就总没人骑。
她没大说出怎么个样,是白天忽来块白云,刚下完雨的天,白得细,又太近,不过一会飘得不吃力,忽一下就从她眼中消失,那个马琛没见到,但是琛都看见她眼和湖压韵。
绿细致了。
刚下过雨,水身上雀斑更加明显,不在意也没用,天又热,也不能常挂个衣服,就都晾,斑一多,是件衣服,他不远不近都没有人注意他胴体,他长得不错,身子撑起来都靠那根——美锁骨,就在这上边,华丽丽朝下撒粒子,他有时被这种阴影相伴,有时闪开,想些事,他也没准经常感激,总之他这人很静。
大家不太能掌握他脸,忽愣愣出来,他总能好躲,后来大家记住些,连上这些年的琛,一想起水,像打从脖梗杀掉,光露得个膀子,却美,他有时就静静掏撸小瓶。
各种各样小瓶。
假说就是那种盛咖啡种子的,他能看一上午,斑斑驳驳,插在小瓶,以前不是,现在是水小瓶子,那天太静,马上就晴天,水忽感无聊,往天上看看见些松,一些松,纵横交错,像相机的一次失误,梦幻啊,松尖细密,他就再来看下边,还是一个小瓶,好好摆桌上,桌是简桌,光滑滑上一滴小瓶,里头种子永远发不了芽,那时光线很足,从茂密一角射下来,没有太多叶子,都是松的针,他一时感到他需要找本书,跑到近帐篷里来,翻来倒柜,还是那本,正在写俩个同性人第一次见面。
第一次见面,他就对他正视,不仅是外表,相当从内心,这都马上使水越发感到种东西,他只好再次看天,天上这时又想下雨啊,但是憋着,就有无穷乱动的飞云,它漂亮着,下视无助的水,就是根豆芽,他又瘦,就那么伶伶着,站在下头。
云在他脸上过,无穷动,无穷动,水下意识了,想起他的雀斑,透着白云,刚洗过雨的棉花照,怎么这么几个斑就这么巧,都要跑到他的肩上来?
往后很多天他们都有夜晚狂欢会。
水都一人,静静也坐,身后是无穷帐篷,他们和她们都早早的,就是晚来的也快乐起来,那升腾起的烟雾,直抵云霄,人都看不见,水看见了,会再注视顶多一俩人,不是她,就是她,是他,他会再次想到那本书上。
琛手里冰糕已经吃完,这时流了一手,天干物燥,发挥的奶油继续发力,轰出阵热气,扑到琛,琛连忙躲,就像一不小心又看到那些年。
这辆车比刚才那辆干净,大家都很老实,谁也不跟谁说话,就是偶尔有些微动静,出现在一个人房前,也就他的那块玻璃,他肩头抖了抖,是为了打破开只小飞蠓子,一个女人又想补装,撩开水粉子,打上蜜陀子厚粉,里边镜片随时反照,这时就是位壮汉,或就是快又睡撑过去的人,琛打量窗外。
这时都罕见的是些树,地面净掉枝子,压过了,躲过了还是巅,巅过来琛再过去,再咬回来根,琛就再加劲挪,不等车正琛腰过不去,她这时极力想一个人,是因。
他脸上也有雀斑。
因那时瞪视琛,琛在想事,她都马上看到这个因,他怎么那样?这时就像从天降,琛面前过来对眼,如小豆粒子,眨眼后是个小孩,琛感到刚才那个因,马上改变了目光,他在看到琛的细部,就是她身后的地方,琛从不知道自己,她细看不怎么想说的小孩,他脸上也有,星星点点。
小孩有意识,又无意识,连续撤退又再回,再踫到琛,不光是眼,有时对着双鞋也认情,这都使琛再次感动,走时还像有话,豆粒子不记眨动,会忽然落下同情,琛这时看着想掉泪,马上别头,看着继续向后走的树,大树,听见她母亲叫唤,一片片树深厚,旷远,毫不留情,有时砸片阴影,也是短暂,涮就过去。
露说那种房子,她喜欢,但没有,露带了自责,显在个脸上,说出来,肉吞吞,她在这几年里真找。
琛听着,争取听完,没完时她都在听出来,露和她长相不一致,露很美,最开始琛见到露,有点怕,就和要是说一句她就走开,这点琛非常在意,就是怕惊散,琛那时也没有朋友。
露美,美在绿眼,但不凶人,有时有点危险,琛都在看,她不怕,露想那种房子时,眼最绿,她讲她就不需要多大的一间,小小,方方,进门就是个坐沙发,这边有台灯,要那种高地的,琛问什么是高地,露说怎么你还经常看书呢,离地面有段距离,挂个帽子,灯光从百折里下射,有时像顶帽子,我可躲,就躲进去,或不躲那就是个阴天,刚下完雨,尽情放眼,窗外都是树,一棵,两棵,三棵,并排,无限湿雨汽,也不蒸,也乱,平平地就从半空掉下来,露看见这些,外边在树下的人看不见,却支起帐子,特别温馨,她们都是一家子,料料峭峭,也不看这种绿树,露在这种小暗屋,看得如醉如痴。
你找到了么,最后琛听完秋虫子叫,才问露。
以后都是这种虫子,像蛐蛐又不是,叫上来是种棉,火绵绵,该亮时琛和露都感到动听。
昨天晚上琛做梦,又回来,但没看见山,就是跑回山房,她知道那边有山,但是看不见,琛在种把持中,向楼底看,又看到几撮女大学生,她们往坡子下增加,几人脚步摆列,就快到坡底,这边一伙消防队员,泡在烈火红衣,开始有纷争,琛努力向下,再努力,最后直接跑到楼下,开始劝架,他们仍在吵,琛和具人体下剩,浑身透明胶,琛来劝真人,回身就拽出个这个,所有人笑琛他已经死,琛不信,她想她脸上也有急,现在在心尖子,她说,哎他还有气啊,大家都没听见。
到最后整个胶都开,她发现这是块木板,但是从一开始琛真看出来,他胸部起伏,那是在呼吸。
房子是琛住过的,最远有山,秋夏盛境,她都想忘,这楼底却总在坡上,坡了30年,继续坡下50 年,60年,或更长,她都在忘的过程,琛在这里死过家人。
琛转回了矿场,这大半天,转来转走还是回来,这倒也不是她的目标?
琛想到粉红色,也在早晨,她半趴窗,就有对街,一队队刚入伍兵得换,一岔岔再上来,都火腾腾地上阶子,兵哥是硬汉,她却感到粉红,继续模糊,继续在压灭,后来她稍一偏头,这边还在童年,已经看出街窄,但都在认真行车,中间犁道栏可爱,她看不见那些童年桐树。
也是粉红。
大家都在,只是进步。
狂欢节上,露,水,因,圆,依,贤,乾,自然见面,少不了琛,这时距矿场花园解散不远,他们不知道。
男女都在说话。
夜,池泛蓝,不像绿,过去有泥巴,晚上有灯泡,贤和乾不想,白天谁争到那个白男人,童脸男又是谁。想不想第二天马上来,开始有人感到东西,不敢说厌倦。
贤努力回忆男人,想到她来这里,贤不断争取,仍然接不上,过去干过的公司,人家都在进步,贤也没落队,但是她身体在落队,再欺骗不了别人,贤这一整年过得简洁加颓废。
争取男人,离开男人,争取男人,周边水草,高一人草,婴婴珊珊,拉不过来,盖不住身子,整天取悦男人。
乾在失意。
她其实小,这琛早看出,胖婴儿肥,拽住个黑胶圈,老是患得患失,这边不是勾手男人,正甜蜜抱紧女人,就是她在湖中,这种浅湖之中,也拉开胳膊,泡在水,呼一个,但是那边老是别人的人,乾在呼喊,或是呼唤。
这种晚上,琛和她共坐,大家开始聊天。
琛问乾乾?出去这里能干些什么。乾不说,视线划条直线,到那头没别人,露,晚上灯光下,她在草中,隔湖见慵懒,这并不能拯救乾,琛看露,过段蓝湖,看乾,记住些水虾,夜里跳跳豁豁,她都感到阵凉意,明天太可怕,不知从哪打开。
林斯莫尔郊外,贝可斯希尔采石场,废弃采石场,砂岩峭壁下蓝色水域,这种时光现在经常闪现,就在每个人心里边,但是他们选择不再看见,当那些过下去的日子。
才来时,因会经常看到琛,那都是他在怒视,后来琛觉得这好像很有意思,她们都被人照顾,因看完就没什么,这里的大家就她俩个,琛还是坐在地草边,因选择继续留下,水波纹围绕,他不断感到上身水,特别舒服,有时他想不起这些,忽然来的,就走开,琛像惦记也远眺,穿过他会得到些杂树,和些调料,撒碎到漫坡草地。
这时,他会看见琛,也回头,半天再回来,还是在水中,天上想下雨他也不走,黄花花的,对他身上芝麻粒,接着琛就不再看他,他总认为琛在认,琛要不小心对视,他左右都无人。
亚洲女士有次支个篷,把蓝裙褪掉,露出细腿,钻个蓝白条半打帐,漫坡高草,围着,不动,地上有布,她可静,光脚边再走一米,有个小车,里边个假婴儿,小手跳跃,天上一片祥和,帐对斜山,插花插藤,琛不知她来历,也不问露,这种当面时间也变少,以前光在怪山见,现在找到露就费时间,琛经常又看别人。
园和依老笑,她们老笑。
琛经常拉郎配,但是从来不知园父母,就是有园时有多人,她们都在不远处睡。
就像睡,她们在西晒,琛有回正走怪道,真邪性,又不是那最高坡,它陡,不平,特别不平,不平着就上来,地上破荆子乱地,扎挣抗拒琛,她脚开始吃力,就不得不往上,看这边是乱藤子,太长,扎扎杀杀,就要到琛眼,那就往右,不想看也是乱绿藤子,黄土地上乱地,把地乱枯,有一会琛真害怕,联续想到魔鬼,太暗了,太暗!你再朝前,就快没道,其实有道,得钻,远看得趴地才过,留个小洞,那是远方,周边都是乱,乱藤子,乱地,乱地上车撤子,乱地上掉乱针,都在扎琛心。
过去以后见到人,她们都安稳躺下,光着身子,手娇嫩,搭凉棚,俩女人,四边草,真埋住她,琛想真舒服啊,她们接着听到,从草地抬抬手底,几只眼滑滑,带动点草,掀了掀,双双回去,凉棚继续一搭,这时天上又像刚下过雨,多雨,绿树湿润,琛打算回去,就在这时发现园。
她抱着个吊胳膊,琛特别恍惚,她不知道刚才那个怪道,再往上看,再斜斜,那又是座小山,还围起来个湖,园就和个圣母样,表情凝重但纯美,黄衣白皮,站在当中一个错层,琛想起再看看这俩人,回回头,园仍面无表情,但很沉醉,她认为这就可能是她母亲和朋友。
埋在水中。
琛现在站的地,就是那天,因有一截胳膊雀斑最多,这过去两年,她记起来,他好把这只手冲进绿水,上边眼正怒视琛。
还看见过晾衣服,水蓝单子,灰毯子,咬在棵半大树,树开叶厚,顶上层金黄碎,都是花,呯呯降下,罩满人间,伸开胳膊,搭上衣服,底下有鞋,无人。
今年琛再打算找都没有,她记得旁边是干路,特别干,何其干也,就像天老不下雨,老不是雨天,那种残存浪漫都刮走,再没有穿黄衣小孩,抱球老笑小孩,拿相机研究女士,身上长雀斑,琛看尽旁边,都是干路。
琛忽然后悔,但是太远,两年也追不回,她想如果当时就问一问,也不会现在这么麻木,想起来总在衣服上辨。
亚洲女士紫衣,园黄衣,因经常没有衣服。
她仍然走在条土路。
过了这,再走,再走,穿湖,穿林,看够蓝,看够黑,就有棵树,女人在这玩,男人没有,就从来没有了,琛走过这棵大树,这时是快冬天,还没冬天,树上没叶子,挂着几个干的,所有杈子向天,这都在追问。
忽就来风,成段打琛头顶,想掉泪,她看不见些人,她们原先,原先都围这种树转,没考虑时间,明天就像今天这棵树,特别茂盛,无限美,无限远,但是能被她们围着。
大家都穿比基尼,没有人格外注意其他人,看自己脚,下边有路,地面生草,匍匍地,铺出明丽,她们就像找得到明天,继续走,尽管无目的,她们来时都残存小目的,来到这矿场,发现太大,大的光明磊落,让她们又短暂丢下时间。
一段时间,本来就认真想想,革去昨天明天能干什么。
会干成什么。
但是一泄如注,矿场太美,她们、他们其实没在抱怨,表面上接受,底子就缓慢,因此晒太阳,谈恋爱,看崖石头,琢磨相素,分不清谁是谁女儿,胖男孩又归谁,俩女人吃男人醋,大家集体懈怠。
过去的一年里,我一直回到贝尔斯希尔采石场,琛经常对自己再说这一句。
就一句。
琛就什么都可悲,想回来,2月有洪水,导致一条塌陷路,就在这条路上盛开紫藤。琛突然非常伤心,非常心急地想找到这条紫路。但是已经没有。
这种紫色开始虚假,琛连续的逛场那就像是外星人,因为空无一人,琛在无人时间去硬生生找条紫色路,这不可笑么?
琛在看紫藤时,也可能有露吧。
琛在看紫藤时,也可能有因吧。
琛在看紫藤时,亚洲女士就在隔山,研究地貌,岩不岩的,她会知道什么?不过是极其留恋,巴望着块小地,短暂的休息,比一切她过的时间都要大,她存些体儿,以免以后透支,紫色女士像说过,她干过某超大公司会计。
琛这时捂了捂嘴,发现这条单人道上有朵更小花。
一年过去,就是两年。
两年了,琛还都在路上,她们呢?他们……她和他们普遍没话,连上经常向她射眼弹的,因甚至没说过,所有人都在怕着,其实也不怕,活脱脱等,忽而散掉。
琛有点打量自己了,大自然美的骤然,就都过来了,这一聚看到些,又继续消失,整整一年,就都真在这生活,现在她常再想,这整个矿场就是个生态系统,非常完整,水是大池,会有淡水,但是发蓝色的一直神秘,她都在和她们议论,或是小范围议论,然后就是高树,何其高也,到处都是,坠个野果子是常事。
应该走了。
坐上了车,回去都快,何其快也,琛都看窗外,她好像看到掉下来东西,她也以为是块肉,不是杂物,往天上一看,下掉太阳般,热火燋燎,可不热死麻雀么?等她再定住神了,又在天上掉鸽子,像鸽子,像麻雀,一只,四只,琛最后数到了4就全程没见再掉这种鸽子。
果然是太热了。
那年应该都在夏天,琛记忆最深也巧也怪,就在了夏天,于是所有人都在穿比基尼,没有遮盖,一切盛开,包不包得住,负不负担,都交于大自然,大自然果然慷慨,装得下丑,也是美,算还没过期,大家都还能有后来目标。
林斯莫尔郊外不小,贝克斯希尔采石场其实有美景,废弃的砖厂、采石场,都一个意思,旷古无人,省得下些场地,和现实隔绝,也继续连接,砂岩峭壁下蓝色水域,过去的一年,两年,他们都在观察,吸收。
琛不断地回到这里,一直是这里。
关键词: